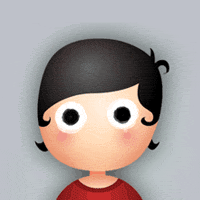我的一生,都是废品
傍晚时候,王福海母亲终于咽气了。那妇人便叫来几个男人,挖了个浅坑,在死人脸上盖了一顶旧草帽,就地埋了。
酒钱必须要从他这一天的生意里赚出来
王福海老人弯着腰、皱着眉,推着一辆小车,用不同的声调喊着“收废品了,收废品啦!”
他推的是一种很特别的,没有车辕的手推车,现在只有黄土高原大山深处的人们还用这种车子。推车的人用腹部抵着车子的后档,身子按照车上所载东西的重量或前或后地弯曲着。这样,一个人就可以搬运相当重的一车东西,远超过一个人所能背负的重量。
这辆车子是他从县城废品站买来的,车把上永远都挂着一个灰黄色的酒葫芦和一个破帆布包,里头装着点儿干馍馍。
每天清晨,他把车从家里推出来,或沿着朝西的一条路,穿过各个小村,不时地叫卖一声:“收废品喽!”直到镇上。镇上有一家较大的废品回收站,他就能将一天收购的废品交到镇收购站;或朝东走去,也是穿过各个村庄收购,到县城也能将一天收购的废品卖出去。
这一带的居民和行人都很熟悉他的这种叫卖声,因为近十年来他一直在这两条路上做营生。
他是一位身材瘦小的老人,蜡黄色的脸上倒挂着一大把鬃毛似的白胡子,末端还沾满了绿色烟叶和白色馍馍渣。他那黑色眼眶里,永远充斥着白色的、如同甲虫的体液般的粘液,里头是一双充满血丝的小眼睛。
有顾客来卖废品时,他就一声不响地拿出横放在车把上的杆秤,默默地称好,连头也不抬一下。有时他也会去老主顾那儿,但很多时候,他总是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地站在村口,撅着青紫的下唇,口角叼一支旱烟。
在他把纸币和铜币乱七八糟地从自己的口袋掏出来的时候,他会瞪眼望着每一个顾客,好像他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似的。
他口袋里的钱装得越少,手车上的重量也就越重。天黑的时候,他恰好到了镇上或是县城里,就会去和废品站的老板结账。一个啤酒瓶能赚到一毛钱,一斤废纸能赚到五分钱。
如果天气很好,‘生意又很顺利’,兴致也不错的话,那么他一天就可以赚到四五十大元,但谁也不知道这个默默无言的老头哪天兴致好,他自己更不知道。
老人兴致的好坏,主要表现在他叫卖的声调上。他在简单地一声叫喊“收废品啦”的声调中所倾注的感情,他所用的抑扬顿挫的调子,几乎没有人能用那么精细的耳朵能把它一一区分出来。
刚出家门的时候,他喊叫的声音是清脆而热烈的,因为在开始工作以前他已经喝下了二两高粱酒,这是他一天的第一遍酒,这酒钱必须要从他这一天的生意里赚出来。
这以后他虽然照常叫着,但他的头脑却已忙着想其它的一些事情去了,事实上只是一些模糊片段的回忆,像一瞬短暂的闪光照彻在他的心扉间。他无尽无休地想着自己的过去,想着自己目前的境况,想着他身外的世界和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
六十八年前,他出生在偏远贫穷的定西山区,谁也不可能想象这个孩子将来会推着一辆锈迹斑斑的独轮车,载着别人的废弃品,在内管到定西之间的村庄叫卖。
他父亲那时候已年近六旬了,家里是一大堆女孩子。头一个老婆给他生了三个女儿,第二个老婆又生了两个。接着就生下了王福海,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
他出生时,家里大摆筵席热烈庆贺的情景,那一带的老人到现在都还清楚的记得。他的记忆中,却没有丝毫关于自己父亲的印象,当时他父亲在一项挖建工程中由于山体滑坡,被埋入黄土中,再也分辨不出。
父亲走后,王福海母亲只能和两个大姐姐耕种几亩荒地,而他的童年则是在捡柴和挖野药材中度过的。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席卷全国的运动蔓延到了那个山村,这时,这一家人才真正解决了温饱,但是吃免费大锅饭的好光景没能持续几年。
有年一开春,几乎所有人家连下种的种子都没有,自然他们家也不例外。到夏天时候所有山川不见一丝绿荫,因为树皮都被剥得净光,一眼望去白花花一片。
迫于无奈,这年五月他母亲就打发最大的两个姐姐外出讨饭了,她们走后一直音信全无。直至十年后,远在内蒙的大姐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了王福海。他才得知姐姐们一直走到了内蒙古,在快要饿死的时候,一家牧民收留了她俩,后来又在那边找人嫁了,日子过得不错。
他的小姐姐们就没交到这样的好运,先后饿瘫在炕上,气息奄奄,直到最后饿死。他母亲将女儿们埋了后,眼见着自己唯一的儿子也快要保不住了,便决定带着王福海外出讨饭。
他们一直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城里走去,一路上不见一个人影,他们只能靠着草根和蹦蹦跳跳的蚂蚱为生。这样走了三天,到了川里时,这才见到了活人。
那天晌午,他们靠在一处田埂阴凉处休息,他母亲有气无力地说道:“福海!俺实在走不动了,你看那边有拔麦子的人,去要点儿吃的好吗?这样我们就能挨到城里了!”
王福海走到那家人跟前,他们正在吃晌午饭。他懦怯地侧着身,站在一旁,眼睛盯住了他们手里的玉米饼子和地上的一只小碗,因为里面盛着黏糊糊的小米粥,而他舌尖距离上次尝到小米粥已是两年前了。
那席地而坐的四五个男人始终一言未发,只是拿眼睛不住地打量着这个面黄肌瘦的男孩。
过了会儿,从远处村庄走过来个年轻妇人,她手里提着一只小木桶。径自走到王福海跟前,笑嘻嘻地摸了摸他光秃秃的头顶,然后问道:“你是谁家的娃娃,在这儿干嘛!”
王福海鼓着劲,说道:“俺妈叫我来要点儿吃的。”
“你妈在哪儿啊!”
王福海指了指远处田埂,这时他母亲正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叫你妈到这儿来吃。”
“她走不动了。”王福海嗫嚅着答道。
接着,那妇人端起那只小碗,让王福海先吃点儿。王福海接过小碗,猛地喝了两大口,碗底已经见空了。妇人笑了笑,掀开木桶盖,盛了满满一碗,叫王福海端给他妈。
王福海接过小碗,朝着母亲走去。他一路走一路吮吸碗沿,结果路还没走一半,碗就空了,他只得折回来。这一切那妇人全看在眼里,她没有流露出丝毫不悦,非常爽快地又给他盛了满满当当的一碗。
这一回,王福海在心里不断抵制着小米粥的诱惑,但他的嘴却十分不争气,不断流着涎水,他决心喝一小嘴,把口中的涎水往肚子里冲一下。当他走到母亲跟前时,他已经冲了三次,碗里没留下什么。
当他端着第三碗走到母亲跟前时,他妈已经不会动了。他叫了好几次都没能叫醒,就把这碗粥也一口气喝了。去还碗的时候,他对那夫人说道:“俺妈睡着了,没能叫醒我就自己喝了。”
那妇人感觉不对劲,跟着王福海到了他妈跟前。那妇人摸了摸她的脸,知道已经没救了。饿死的人妇人见了太多,知道人到这种程度,再吃什么都不管用了,因为萎靡的肠胃已没有能力吸收更多养分。
傍晚时候,王福海母亲终于咽气了。那妇人便叫来几个男人,挖了个浅坑,在死人脸上盖了一顶旧草帽,就地埋了。
当王福海回想往事时,他感觉那是一种无尽疾苦的生活,但那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遭难生活很快就消失了。
那天晚上,妇人把王福海领到了自己家,在柴房里铺了一张席子,还给了件破军大衣叫王福海盖在身上。第二天,妇人便叫王福海跟着自己生的一个大男孩去放羊,过了几个月后,王福海正式成了这户农家的羊倌。
任何工作都是艰苦的,就连放羊也不例外。以前妇人家自己孩子放羊的时候,只要晚上赶回家时羊没有少,关进羊圈就行了。但轮到王福海就不行,男主人每晚都会守在羊圈外面,细细察看每只羊的肚子。
如果有哪只羊肚子的鼓胀程度没有达到他的标准,或是因光线太暗没能看清,王福海就会遭到一顿痛骂,有时还会因此失去晚饭。更糟的是,有几次母羊在夜里生了羊羔,被其它的羊踩死了,这样等待他的便是一顿毒打。
一切事都是无法估计的,过了今天谁也不知道明天会遇上什么样的事情。一个人能够知道的,就是他每走一步都会有一颗石头绊他一下,每走三步就会摔一跤。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生活也就一天天失去了光彩和情趣。而那些光彩,正是像王福海这样饥渴的人本能地全力以赴要得到的东西。这种日子他挨了十年,直到他结婚。
“收废品了,收废品喽!”
这种特别的羞耻感,只有王福海才会了解
王福海二十岁时,那个男主人,也叫李爹,想让他成家,不再寄住在自己家里。
当时王福海住在他家羊圈旁的窑洞里,那窑洞是用晒干的土坯拢起来的,上面是拱形,长满杂草。窑里面有一个土炕,还有一个灶台和一张用木板订成的饭桌。五六年里,王福海的吃住都在这个破窑洞。
为了结婚,李家人在那个窑洞旁给王福海新拢起了一间,当作婚房。新娘则是在一个名叫‘后湾’山区用毛驴托回来的。王福海至今还清楚的记得,那天他穿上了人生中第一套新衣服,还戴了朵大红花。
当时新娘只有十五岁,爹妈早死了,跟哥哥嫂子住在一起。劈柴生火,推磨簸麦无所不干。她嫂子为了弥补失去这个免费劳动力的损失,还跟李家人要了整整五升麦子和一只大公鸡。这对当时的王福海来说是一笔庞大债务,他注定要用很多年才能还清。
结婚以后,李家人就让王福海去山上给自己开垦一些荒地自力更生。在过去,严格地讲,他根本不知道“自力更生”这几个字的意思,也从来没想过。
既已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他才开始认识到,在这个简单成语的背后潜藏着多少苦痛和悲哀。不,并不是他所要从事的工作如何繁重或困难,只是使人感觉到有一点卑微、下贱。
他连一把属于自己的铁锨、一粒小麦都没有,所有东西都只能去向别人借。而每一句话,每个动作都似乎表现着某种说不出的屈辱。这是一种特别的羞耻感,只有一个身为王福海的人才会了解,这种屈辱只有用高粱酒才能洗去一些,但也只是暂时洗去而已。
时间一年年地过去,情况并没有好转,甚至连梦里所见也是一无所有。家里破烂不堪,肚子吃不饱,没有一件完整衣物,他们始终无法在人前掩饰自己的穷酸状。那几年生的四个孩子,只有一个男孩活了下来。
他慢慢长成了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王福海想尽办法,才将他送进村里的小学念书。也许是父母的智力一直空闲着,没有得到利用的聪明全都遗传进了男孩的脑瓜,所以他在学校功课很好,手里总是拿着几页破书。
很快他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初中,开始在离家十里的李家咀上学。三年后他又考进了市一中,开始在学校寄宿。但他在城里上了两年学以后,却莫名其妙地被同学打死了。
据说是因为和当时校长的女儿谈对象,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在一天夜里,和同学发生冲突时不小心被人打死了。
在这期间,王福海老婆又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但他老婆生过小女儿以后,就一直不能下炕,最终因为身体虚弱不治身亡。
这时候,命运的魔爪还没有夺取他的希望。他千辛万苦,用羊奶和玉米面糊糊才将这两个孩子养活。小儿子长到六岁时,王福海也将他送进了学校,期望他能像大儿子那样成为人人称赞的‘小神童’。而自己也能在别人的艳羡中感到几丝优越感。但遗憾的是,这个孩子没有表现出多么过人的智力。
说实在话,他的智力应付不了学校的功课。并不能说他比其他的一般的孩子更淘气,只是书本上的东西始终没能装进他脑子里,他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些更远的东西。
初中还没毕业,他就离开学校混迹在定西城里的一帮小流氓中间,跟寻欢作乐的生活打上了交道。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整个生活就是消费掉他父亲千辛万苦开垦出来的土地,和用两只母羊繁殖出的羊群。
但王福海是一个毫无主见的人,所以,根本没有人阻止他从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或把他领到一条正路上来。生活中的一切对他都是那样新奇,好像完全是为了他和他的朋友们而特意创造出来,供他们恣意享受的。这种日子一直延续到了他十八岁。那年春节过后,男孩一声不响地和几个熟识去了新疆。
接下来的几年,王福海依靠种地和放羊积攒下了些许家底。盖起了三间土坯瓦房,安上了玻璃窗,才算正式告别黑魃魃的窑洞。这时候,他那个唯一活下来的女儿也出嫁了。丈夫是一个建筑工人,受过初中教育,当过兵,算是个极有出息的青年了。
他比她大不了几岁,但经济状况也并不比她父亲更好一些。因为他母亲生了六个女儿,四个儿子,结婚以后没能分得多少家产,只剩下一间瓦房和一头小驴。
女儿离开以后,王福海经常喝得醉醺醺。这时村里很多人都对他议论纷纷,空讲是很容易的,却没有一个人能说出究竟他为何酗酒,或者为什么要这样!
“收——废——品——啦!”
那一年是王福海记忆中最幸福的一年
王福海孤身一人过了三年,第四年他儿子回来了,并且带回来了一个女孩。姑娘是少数名族,只有十八岁,生得极为漂亮,回来没几天就轰动了四里八乡。
当他得知那女孩已怀了四个月身孕时,兴奋得几夜未眠,决心要为儿子筹备一个盛大的婚礼。他一生还未光彩过,这次一定要在乡亲们那里涨涨脸面。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婚礼当天,来了许多不认识的人,有小镇上的商贩,也有县里的上班族。
为的就是看一眼这个维族姑娘,王家也是来者不拒。这天三更,王福海就亲自宰了三只羊,他要让所有的客人美滋滋地吃了一顿羊肉泡馍,这在当时的乡里可算盛宴。
但婚后不久,他儿媳就因水土不服,一病不起。他们找来了县医院的大夫,打了三天吊瓶才慢慢好转。总的来说,儿媳在整个妊娠期都小病不断,但孙子总归顺利出生了。
此后那一年,是王福海记忆中最幸福的一年。不仅对这个家信心十足,就连不务正业的儿子也务实起来了。他儿子在庄稼都种上以后,在城里摆了一个卖羊肉泡馍的小摊,用的是自家羊。在新疆的这些年,他学会了维族人做羊肉的方法,所以味道非常正宗,生意十分红火。
第二年,他们发现小孩子有些不正常。虽然学会了站立,但始终发不出清晰的口音,只会咿咿呀呀地叫唤。在这种恼人的不安下,又过了一年。这个两岁的男孩目光呆滞,不懂得表达自己,也始终没能学会上厕所。
家人带他去医院做了详细检查,医生的结论是:这个小孩患有先天性的脑瘫,治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二天,王福海儿媳一声不响地就走了。而他儿子则带着孩子走上了四处求医之路,省城、西安、北京。用最先进的仪器,吃最好的进口药。没半年,这个家便空空如也,还欠下了一屁股债,但孩子却不见丝毫好转。
每天都有讨债的人和放贷者守候在门口,孩子爸爸终于支撑不住,悄悄的跑了,这个家又散了。
接下来的十年,王福海起早贪黑,种地放羊,债务差不多还清了。这时,国家开始了退耕还林政策,山里面不准再放羊了。因为多次违反规定,他的羊被一班人赶走了,留下的钱远远少于这群羊能卖的高价。
王福海一生都在放羊,除了放羊,他已不懂其它的挣钱方法。女婿看不下去了,便给岳父买了辆手推车,让他去收废品。
王福海不能忍受这种屈辱。虽然从那时起,他才真正开始喝酒,开始推着一辆手车四处游荡。也是到这个时候,他才对整个世界抱有一种厌恶的感觉。是的,至少别人都这么说。但他清楚地知道,那并不是事实。这话绝对真的!
他并没有厌弃世界或厌弃工作——天知道——相反的,世界上的一切,有生命和没有生命的东西,以及人所想象的、所做的或所说的都一天天离开他,更远了,把他独自留在一个泥坑中,痛苦不堪。
在那里,只有一两高粱酒能带给他一点光明,还能为他歌唱。还能像一个女人的手一样抚摸着他,还能发出花一样香甜的气息。其它的一切都迅速地、毫不留情地抛开了他,高粱酒是他现在唯一的安慰了。
他解下,挂在车把上的酒葫芦,猛地大灌了两口,高粱酒火辣辣地灼烧感,穿梭在五脏六腑。他扯开嗓门,高声叫道“收废品啦,谁有废铁、废纸、空酒瓶啊!”
在他喝醉时也没把这个秘密透露出去
从那以后,他像个游魂一样和整个世界彻底隔绝,越来越失去了控制。他女儿亚娟,虽然住在定西城的郊区,但境况也不是很好,只有她才来看他。女儿是那样美丽、娴静、愉快,他感觉她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人。
最初她还常常劝导父亲,求他把酒戒掉,好好振作起来。但是很快她就看出这样做是没有用的。以后她仍照常来看他,但不再说一句规劝的话。
夜晚在酒馆时,别的醉汉们天南地北地瞎吹。于是,王福海也对人们夸耀起了自己的儿子儿媳。
“我那儿子儿媳可真了不起啊!听哪,呵呵,听哪!他们……他们……啊!俺不知说啥才好……”他会一边打嗝一边对酒馆里的酒友们说。
但接着,为了消除心头的痛苦,他会再多喝几口高粱酒,就立刻忘掉了自己的儿子和儿媳,甚至忘掉了自己,只留下一个傻孙子在他眩眩晕晕的脑中打转。
而他生活在这个如同云雾中的世界里,从来没有注意过那些不喝酒的人在干什么、那些清醒的人整天在什么地方活动。直到有一天,他听人说,新疆发生了一些事,有很多人被打死了。
王福海心想,这可能只是一次小流氓骚动或劫掠事件罢了,自然是比他更年轻的人的事情。可这次事件似乎有些不同,连他也多少有些异样感觉。
王福海推着他的手车,机械地喊着那几个字——如他机械地喝着他的酒,机械地呼吸着一样。既被世界所弃,又与世界完全隔绝,他也许感觉不到任何改变和任何新的麻烦,就这样平平安安地度过这次事件吧……
然而,一件他完全不能理解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早上,家里莫名其妙地来了几个警察告诉他,,不久就要被判刑。他想尽办法,苦苦哀求,一个胖乎乎的警察告诉他这是‘法律问题’。
告诉他这话警察,说完话耸了耸肩,闭上眼,伸出一个手指头按住了自己的嘴唇,王福海不知为什么也学着那人的姿势做了一下。
后来有一天,邻居孩子把一张照片拿来给他看。王福海昏花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他认出这是他儿子的照片,不过比他过去见到他的时候变得矮小了一些,变得瘦弱了一些。王福海看到这些心都凉了。
那个邻居告诉他,新闻里、报纸上都说他儿子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还讲到了酒的可怕;他的态度是那样的亲切,但王福海却觉得自己离他是那样的遥远,他为什么要对自己讲这些话呢?
在酒馆里,大家所谈的关于他儿子的事。他们讲的话他并不十分了解,听不懂,但他却躲到一旁偷偷地哭泣了起来,他咬咬自己的嘴唇,最后是和着更多的白酒咽下了自己的眼泪。
要使他尽可能地忘掉这些事,不再去谈论它,那就需要大量的白酒。此后,他的酒越喝越多,饭却越吃越少了。有时候疼痛的心和他原有的几根硬骨头也使他深感到必须要据理力争,但这些感情,很快就消失在那些荒凉的乡间小道上,和他的一声叹息或一阵哭泣声中了。最后则是一葫芦白酒淹没掉了一切。
现在他除了一个傻孙子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除了女儿以外,再没人关心他。他的身体已经衰老不堪,衣服破烂,脚下几乎连一双鞋都没有。一切都消失在挂在车把上的那只酒葫芦里了。
“收——废——品——了!收——废——品——啦”
他正用全身的精力将小车推到那边的小山
接着他又忘掉了这一切,照旧推着他的手车走在土路上。为了烟叶,为了高粱酒,为了……甚至为了他的一顿饭,两个大饼,他必须设法赚一点钱。
满脑子装着这种思想,他来到了村委会的大门口。他常常从这里穿过大马路走近一些狭窄的陡峭的小街道里面去。有一阵学生唱着少先队队歌从学校里走了出来。
王福海停下来,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曾经是少先队员,他们也唱过这首歌。他不懂他们唱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这时朝那个方向去或为什么排着队在路上走着。
那一队孩子走过去了,他们的歌声却还听得见。接着又是一阵骑着自行车的大孩子,他们照例唱着歌,不过那些是情歌。两群人的歌声融合在一起,歌词和歌调混成一片。他身旁的每一个人都在歌唱,每一个人都欣喜地从他的前面走过。
一切都是这样有秩序,有纪律。但很快,这些人都慢慢从他的眼前消失了,都到别的地方去了,远远的离开了他。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走开,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这一切他都不了解,感到腰部隐隐发痛之外,他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感觉。每当风从东方吹来的时候,他的腰部总隐隐发痛。但这种痛苦并不能使他想起任何事情。
因此,当他推着手车走进第一条巷子的时候,他禁不住想大声喊叫:“我那两个儿子可真了不得啊!听啦,你们都听哪!他们……啊!俺不知说啥才好……”
他轻松愉快地推着他的车子,仰着头用一种粗哑的声音喊着“收——废品啦。”
在路过村委会办公楼时,二楼的一个年轻女人叫他,要他上去取一些旧报纸,不要钱的。王海福老人立即毫不犹豫地、傲慢地拒绝了。
“这儿堆了一大堆,快呀!我另外再给你一块钱还不行吗?”
“我不能替任何人把废品拿下来。你给我一块钱也不行,就是给我一百块钱也不行,懂吗?如果你要卖货,就自己拿下来!因为这是买卖,就应该公平。”
那女人在他身后恶毒地叫骂着,但他已听不见了,因为他正用他全身精力将小车推到那边的小山,一面光明正大的叫喊着:
“收废品啦!收——废——品——喽!”
——END——
本文版权归“弋叶行”所有
每周三、周六,
跟我们一起窥探平行世界里的人和故事。
长按关注“平行生活实录”↓↓↓